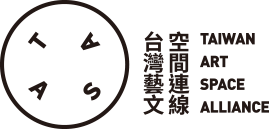文|黃星達 博士
2025年5月17日台灣藝文空間連線TASA協會在台北IMPACT Hub舉辦《維度初光 — 政策下的文化影響力與永續可能》工作坊,以「文化影響力」與「永續發展」為雙主軸,試圖搭建一座橫跨於文化政策與實踐現場的對話橋樑。參與的跨界人士包括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牯嶺街小劇場、SUP Taiwan、洛德企業、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及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等代表。透過面對面的交流,激盪出政策思維與文化實踐間難以迴避的結構縫隙討論,不僅為文化永續提出新想像,也促進與會者重新審視制度設計如何與第一線實作現場建立有機連結。
從資源分配到藝創條件:制度落差與文化支持的結構縫隙
當代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實踐之間,有時會出現一種難以忽視的理想與現實落差。許多長期關注藝術文化政策者發現,藝文補助制度多半聚焦於資金配置,卻忽略藝術家於實際創作過程中所面對的技術支援、材料流通、生活條件與制度彈性等基礎環節,如是,以文化政策促進文化生產的永續發展即有所受限。藝術進駐政策常以「空間」作為實踐成果,其效果其實流於形式,無法回應藝術現場的多元需求。文化政策在防弊與促進之間,往往有更多的機制希冀能有所完善,對此,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藍恭旭總監指出,但像「臂距原則」這類制度性保障,若無法在執行層面有效落實,將削弱藝術自主性的真正意涵。當政策中「共融」、「多元」等關鍵詞無法回應實際運作機制,也終將淪為政策敘事的空殼。因此,文化永續的實踐不應僅止於場域提供,而應從創作生態鏈整體出發,建構一套能連結補助設計、制度彈性與執行資源的支持系統,讓創作者得以在穩定條件下展開長期探索與創造。
此一結構性落差不僅發生於國內文化治理,也可延伸至區域與跨國文化交流策略之中進一步思考。在新南向政策脈絡下,文化如何轉化為促進制度韌性與深化區域連結的中介工具?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陳韻竹助理研究員提到,文化外交的核心價值應建立於「對等交流」而非單向輸出,該基金會辦理許多如青年交流、電影放映與藝術論壇等實體活動,逐步培養跨國文化理解與民間連結的厚度,方能賦予文化政策更具彈性與在地能動性的實質意義。正如TASA團隊所強調,文化政策若無法回應第一線實踐者的經驗語言,即使具備「永續」與「影響力」的理想,也終將失去其具體效力。因此,文化永續的實踐必須回應包括文化價值、社會包容、經濟運作、生態共生、心理福祉與平權參與等六大核心面向,使政策得以從理論層面進入行動框架的具體落實。
從單向深化到跨域共創:文化影響力的延展維度
順著上述制度設計與行動場域間落差的討論,本段進一步指出:唯有透過跨域協作與多元角色的參與,文化影響力才可能從單一場域的深化走向可持續的擴散與轉化。SUP Taiwan 聯合執行長黃鋆庭強調,藝術從未應被視為與生活割裂的孤立實驗,而是一種深具公共參與潛力的實踐路徑。2025年其與英國 Salford University 推動的雙向駐村交流計畫,展現出藝術如何作為回應在地、增進理解、強化教育與文化自覺的具體方式。學生不僅提升語言與創造力,更學習如何在文化差異中重構自我位置,體現文化公共性與地方行動的交織成果。
而文化的延展,亦可由產業面向提出另一條可能路徑。洛德企業董淑惠創辦人指出,企業參與文化不應侷限於贊助模式,而應進一步成為文化共創的實踐者。在全球高度商業化的時尚產業中,企業若能導入文化敏感性與永續意識,即可創造新的品牌意義與公共價值。她以北投文物館活化案例為例,說明企業透過策展思維與異業整合,得以轉化文化敘事為可見的公共經驗,體現共創、共識與共享的文化經營模型。由此可見,跨域合作與多元場域串聯,不僅拓展文化影響的可能,也為文化永續開啟結構性轉化的新路徑。
從文化參與到日常實踐:公共性重構與人本轉向
若說制度修補與場域擴展是文化永續的基礎工程,那麼文化能否真正進入人的生活、轉化為日常中的公共經驗,則是其深層實踐力的關鍵所在。牯嶺街小劇場姚立群館長認為,劇場不僅是展演藝術的載體,更是參與、對話與身體感知再啟的公共場域。透過如「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的實踐,將視障者、高齡者與成人教育參與者納入創作脈絡,劇場得以成為激發感官經驗與世代理解的場所。唯有藝術能回到生活日常,文化永續才有可能在人的感知與行動中真正落地。他強調:「藝術的意義來自交流的發生與樂趣的醞釀,而不只是成果的呈現。」
延續此觀點,SUP Taiwan 聯合執行長 Amit Rai Sharma 也強調,藝術教育不應只強調知識輸出,而是應以共學與共構為核心。在駐村創作中,藝術家所帶來的最大改變,往往不在於展覽成果,而是日常中建立的情感連結與文化理解。然而,這種深層交流若缺乏制度支持與長期資源,其影響將難以延續。他提醒:「藝術家離開之後,如何讓這份能動性持續在地發酵,是文化永續的核心課題。」唯有建構延展性的知識傳承機制與穩定的資源支持網絡,文化交流才可能由點轉面,形成長遠的文化轉化力量。
此一文化的日常化與倫理轉向,也可見於博物館的當代表現。現任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秘書長表示,博物館已不再是知識權威的象徵,而應轉型為社會參與與倫理實踐的平台。面對族群多樣性與社會變遷,博物館的永續責任不只關乎能源與典藏,更在於價值選擇與制度抉擇。無論是原住民、新住民共創、特殊族群參與或數位出版等行動策略,皆體現出文化機構的角色正在從象徵性的展示場,轉化為文化平權與倫理對話的節點——不斷回應「我們為誰而存在?又該如何存在?」的本質提問。這正是文化永續從制度規劃走向日常實踐、從資源分配落實到人的參與經驗之深層轉向。
從人出發:文化永續的三重省思
文化永續不僅為一項政策,它更深植於制度選擇與資源分配的倫理中。每一筆預算、每一項補助,實際上都代表著一種文化的選擇行為。這不僅是對有形資源的分配,更是對價值觀的選擇與實踐。因此,在推動文化永續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反思:我們的資源如何配置,哪些文化表達值得被優先支持,這些選擇背後所承載的倫理與社會意義是什麼?當永續成為一項價值抉擇,才能確保文化政策在實踐中不僅符合當前的需求,還能引領未來的發展。
文化的真正意義始終與「人」的轉變及生活的改善緊密相連。因此,當我們談論文化永續時,必須關照到不同群體的處境,特別是藝術家的創作條件、高齡者的學習權利以及身心差異者的參與可能。這些議題提醒我們,文化永續不僅是資源與制度的問題,更是關乎人本身的問題。只有當我們真正關注到各個社會群體的需求,才能夠確保文化的多樣性與包容性,並為所有人創造更有意義的文化生活。
此外,從多位講者的實踐經驗來看,文化工作的推動往往從個人的關懷與行動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擴展至制度轉化與社群共創的層面。這一過程不僅彰顯了文化的深層影響力,也顯示文化永續的深層力量。文化工作者的個人行動,最終也許相對更有機會影響制度的變革,並透過社群的集體力量實現更大範圍的文化影響。因此,文化永續的實踐並非單一的事務,而是一個由內而外,從個體到集體、從在地到全球的擴展過程,同時,也因著由外而內的影響,持續加速藝文環境整體結構與制度治理的滾動式變化。
從回應現場到形成制度,文化永續的行動起點
《維度初光》作為政策與實踐者的交流設定場,在與談者充分暢談理念與行動臍帶後,更重要的還有接下來應如何思考整體藝文環境的發展,甚至如何實踐、如何溝通,或如何說服。未來若能持續深化對話、累積案例資料、納入更多實踐者的語言,將有助於構築一套兼顧彈性、創造性與前瞻性的文化永續政策架構,真正回應當代社會或臺灣的複雜需求與文化轉型。
黃星達
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組長、現任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秘書長。曾赴美交流非營利組織營運評估與跨文化議題。近年投身藝術行政與博物館領域,期待透過深耕教育與藝術的領域,開出能傳遞文化芬芳的花,並在花開花落間延續著溫潤的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