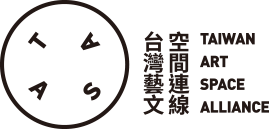文|黃星達 博士
《橋樑與對話—藝術進駐的行動實踐》為「維度初光」焦點論壇系列的第二場,於2025年4月20日假台北 NPO 聚落舉行,以「藝術進駐作為連結藝術家、社群與制度的中介」為範疇,探討駐村作為文化交流平台的多重面向。七個長期參與藝術駐村及文化實踐的機構,包括鴻梅國際藝術村、超級浪藝術空間、利澤國際偶戲藝術村、新樂園藝術空間、駁二藝術特區、邊邊女力協會及湄公河文化中心,分享各自的駐村策略、面臨的制度挑戰及在地行動經驗。
行動實踐與空間協商:藝術沒有空間限制
本場講者多以駐村作為打開地方感知的觸媒,強調藝術進駐不僅是「進入」地方,更是一場持續協商與再配置的行動過程。鴻梅國際藝術村執行長林靜雯回望其從零開始建構藝術村的過程,從規劃、設計到施工、駐村運營幾乎一手完成。她強調藝術村不應只是藝術家的工作基地或展示場,而應與在地文明、地景與文化記憶互動,生成真正的「場域精神」。她以駐村三階段計畫為例:藝術家進駐後需從在地生活開始,再與社群互動,最終以作品或行動回應場所。這種從地方出發、強調關係生成與過程參與的模式,也延伸至新竹市區老屋中的日常空間展演,並透過 Podcast、線上導覽等形式,擴大駐村行動的可見度與持續性。
超級浪藝術空間共同創辦人林思瑩以宜蘭羅東的「超級浪」空間為例,提出駐村應讓藝術家重新生活、重新創作的理念。她坦言羅東的藝術能見度不高,故設立台北發表空間作為都市與地方的連結節點。同時,她分享過去招募學生藝術家駐村的嘗試,發現與地方的連結不易建立,遂決定未來聚焦具備創作主體性的藝術實踐。她認為駐村制度需具備開放性與彈性,國際連結亦不全倚賴徵件,而來自展覽交流與人際信任的累積。
鴻梅國際藝術村透過陶藝、染織等與地景結合的工作計畫,使創作深植生活紋理;超級浪將藝術家置於羅東日常中,實踐「生活即創作」的理念;新樂園從台北移動到桃園的轉型過程,則從桃園市場到鐵道邊地景,展現進駐與場域之間多層次的對話。這些行動策略顯示,空間不再是藝術的背景,而是生成藝術行動的主體,藝術家須在其中不斷調整、自我定位,以回應場所的邏輯與現實。
感知經驗中的他者與行動:在藝術感受與理解中找到安適
利澤國際偶戲藝術村藝術總監 Helmi 以「逃離日常」為駐村設計出發點。他指出,藝術進駐不應僅著重成果,而是讓藝術家在異地獲得休息與靈感重啟的過程。利澤提供安全、安靜的生活空間,鼓勵藝術家調整原先提案,並安排與地方文化、社群的交流活動。他提出駐村不僅是創作者的修復,更是與在地互動的橋樑,強調「過程」的重要性遠勝於「展示」。目前利澤正與加拿大、墨西哥發展「雙向駐村」合作,擴大國際文化網絡。
邊邊女力協會空間經理陳冠蓉分享 2024 年首次舉辦的「女性主義創作者小聚」,聚焦數位性別暴力與創作心理安全,她提到過程中面臨的創傷情緒與照顧倫理挑戰,強調此類駐村型活動必須納入情緒支援與療癒設計,否則將難以承載深度議題。此次活動不僅促進東南亞與台灣創作者的互動,也反映小型團隊在執行高敏感度議題時的實踐難度與策略彈性。
藝術進駐同時也是他者經驗的樞紐。邊邊女力的「女性主義創作者小聚」從料理、圖像交流出發,逐步觸及數位性別暴力的創傷經驗,闡明藝術進駐不但要輸出共感,也應建構「心理安全」的關係結界。MCH 與利澤藝術村則強調以人為本的進駐哲學,不是要求藝術家產出什麼,而是邀請其重新「感受土地」、「理解他者」,進而生成跨文化的情感連結。這些實踐凸顯藝術不只是表達工具,更是一種具倫理意識的行動方式,需在他者面前練習聆聽與共同構築。
制度條件與協作實踐的落差:從Reproduction到regeneration
新樂園藝術空間總監張雅萍分享其多年從「藝術家個人實驗」到「集體制度實踐」的過程。她特別提到「菜市場駐村」的經驗,嘗試將抽象的藝術語言轉譯為地方居民能理解的溝通方式。新樂園採開放的集體自治制度,每兩年更換大部分成員,保持組織活化,也承擔著制度不穩定帶來的壓力與創新張力。張總監強調駐村成果不設形式與框架,主張藝術應深入地方脈絡,讓行動成為關係與語言的中介。
來自湄公河文化中心(MCH)的計畫統籌李慧珍以「Meeting Point」年會計畫為例,說明組織如何扶持亞洲實務文化人進入國際對話場域。她強調「不找最厲害的人,而找最需要機會的人」,並以「媒合」與「陪伴」為選件核心,回應主流國際平台常忽略邊緣地區工作者的問題。2025 年 MCH 將於寮國永珍舉辦年度主題為「Building Bridges」的年會,並設有台灣獎學金( fellowship)以支持本地文化人進入亞洲網絡。
作為台灣唯一由公部門直營的藝術駐村計畫,駁二藝術特區副主任徐異宸介紹其以港口歷史為發想的「藝術進出口」策略。駁二強調駐村不僅是地方資源的引入,也應是藝術與文化能量的輸出。其與多個國際城市與國內機構合作,發展互惠的駐村交換平台,同時亦調整駐村規模與制度設計,以提升陪伴深度與後續發展的可能。
從民間機構如新樂園、邊邊女力到公部門體系的駁二藝術特區,皆凸顯制度設計與藝術實踐間的張力。駁二在行政規範與創作自由之間尋求彈性平衡,新樂園則在資源極限下以共治模式維持開放性與實驗性,邊邊女力面對敏感議題時則特別意識到組織能力與參與者心理支持之間的落差。MCH 提出以非菁英導向的選件標準與長期陪伴的支持機制,作為回應制度不對等的重要策略。這些經驗提醒我們,駐村不應只是行政流程的再生產,而應是制度可塑性與文化行動共構的實驗場。
To be continued:未定形仍持續變形的當下形狀
從講者分享中可見,藝術進駐不是單一計畫或展示成果的包裝,而是穿透空間、制度與人際關係的具體文化實踐。無論是以生活為創作場的羅東駐村、聚焦女性創傷經驗的小聚活動,還是以跨國交換為策略的利澤與 MCH,皆展現藝術作為行動、共感與連結之網的潛力。藝術進駐的未來,將不只取決於資源規模與產出成效,而更仰賴各種「能談、能改、能共構」的制度柔韌度與關係密度。
在制度可能更形鞏固、地方性問題愈趨複雜的今日,藝術進駐或許正扮演著某種基礎建設的角色,它為文化行動者鋪設通往現場、社群與制度對話的路徑,也讓藝術在未完成中保持重構與再生的力量,不僅是制度的中介,亦是所有人事物的文化媒介。正如會中所言:「藝術駐村是一場未定形的協商。」這場協商,將持續召喚我們重返現場,重思藝術與社會如何共生共構、共存共好。
黃星達
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組長、現任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秘書長。曾赴美交流非營利組織營運評估與跨文化議題。近年投身藝術行政與博物館領域,期待透過深耕教育與藝術的領域,開出能傳遞文化芬芳的花,並在花開花落間延續著溫潤的韌性。